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信息技术占统治地位、而思想相对贫乏的时代,大多数人被物质功利所诱惑。既想得到物质和功利的满足,同时又意欲摆脱此中的纠缠与负重。灵魂深处充满了痛苦与不安,人也因此迷失在自我构建的荒原中,人生诸多意义被不断遮蔽。
欣喜的是,现实中还有另一类人。他们将一种诗意的生存引入生活,每当劳顿困乏之时会仰天而问:难道我,所求太多以致无法生存?

一
就我所知的周建华,从一名小学教师到德阳市教育局的一名干部,许多年里,一直处于“既为机关干部又是作家”的状态。在命运的摆布下,一站接一站地继续着他独特的人生旅程。从最早的孝泉师范读书,到德阳东电小学教书,再到德阳市教育局……人生轨迹在常人眼里就是一道道纯属辛劳的散乱弧线。人生履历也从教师、机关干部、德阳市教育作协主席等林林总总的角色变幻中,留下了一条虽光亮闪烁、却找不到什么规律的线索。
种种探寻与追问,却忽视了一个不变的因素或者说身份——作家,这个称谓不算明亮,不被通常人所知,更不被通常人看重,却像一种神迹,实实在在地使生活中一些人(更包括周建华在内)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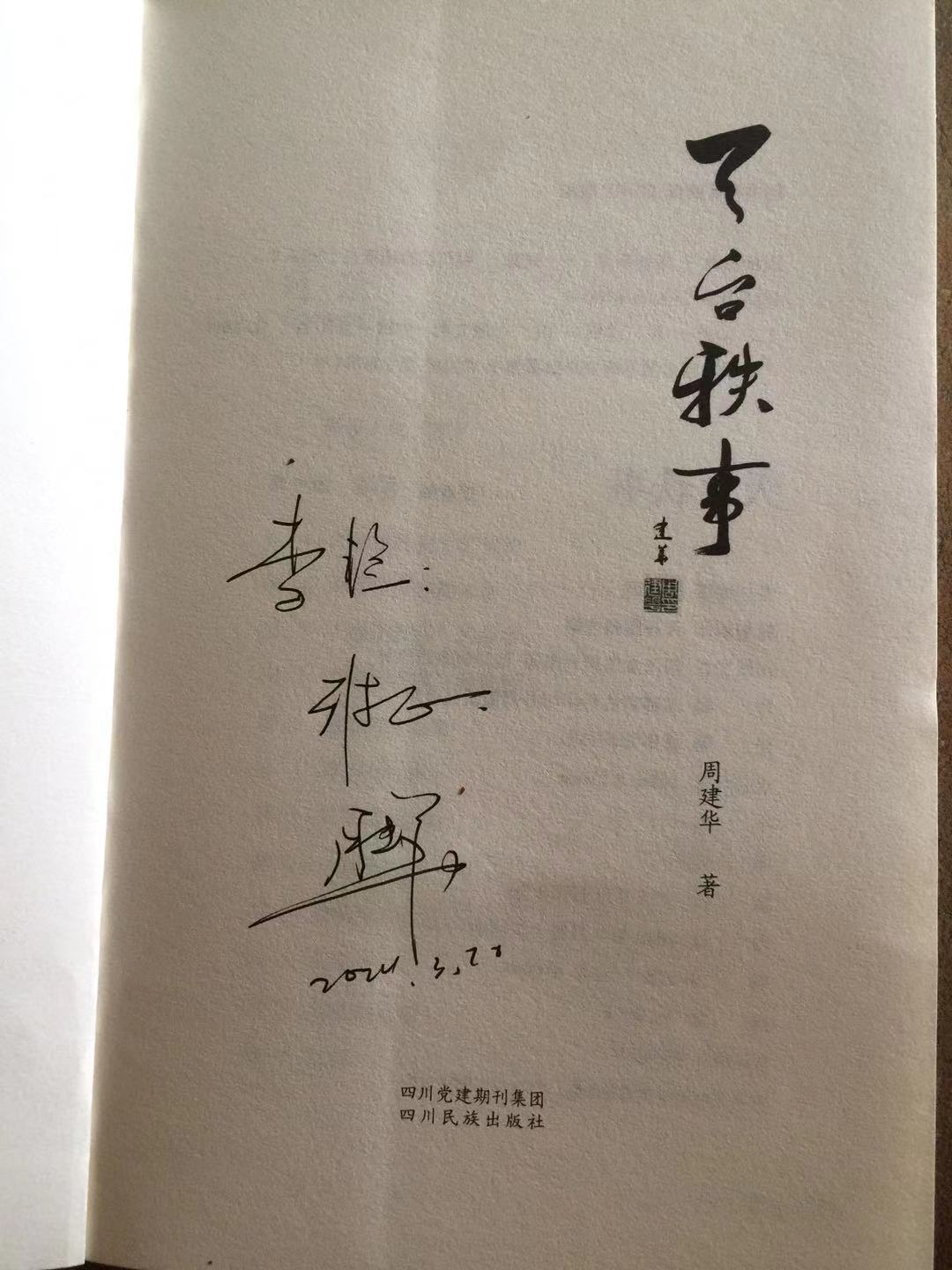
2021年春天,我在动荡不定的天气里读周建华的处女作《天台轶事》。既没有欲罢不能,也没有在哪儿戛然而止,就这样时继时续地进行着,感觉书中的人物和场景,在眼前慢慢活了:“几分钟,从堂屋后面走来一路人,打头一位,是五华宗亲联谊会副会长周锦贵,个子比较高大,面带微笑,一见到带着大家出来迎接的周运生,便紧紧握住了周运生的手。那种紧握,充满了见面的渴望……双方都知道,对方跳动的血管里,有同一个祖先流传下来的血液。[雁1] ”“周玉胜老人走到神龛前,没有像其他宗亲一样揖拜,先是久久凝望着神龛,那种凝望,仿佛要洞穿时空……”怎么看,怎么像是在说我自己,几百年前的湖广填川留下的,是整整几代人的记忆。
一个被平缓打开的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周建华让他近些年来经历过的地方和人物都走到了开阔地带,一个纯粹、纯净的性灵依着周建华认同的方式生长并行动着。

二
《天台轶事》差不多是周建华进入创作领域以来散文创作的全貌。文集从前到后捡选了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,从二十年前的《昭觉支教行》《神圣的使命》,到十多年后的《龙苍沟的瀑布》,再到2017年因修家谱开始的家族篇,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没有遗落,但还是以2018—2019年创作的居多。想来应该是因修家谱修出个周家几百年填川史,让周建华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读后最鲜明的感觉是:《天台轶事》不是小说,却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批人物形象;《天台轶事》不是传记,却提供了作者早年的一大批鲜为人知的传记材料;《天台轶事》不是历史书,却使人从中看到了湖广填川以来德阳历史的若干重要侧面;《天台轶事》更不是民俗学著作,但它却涉及并记叙了不少城乡风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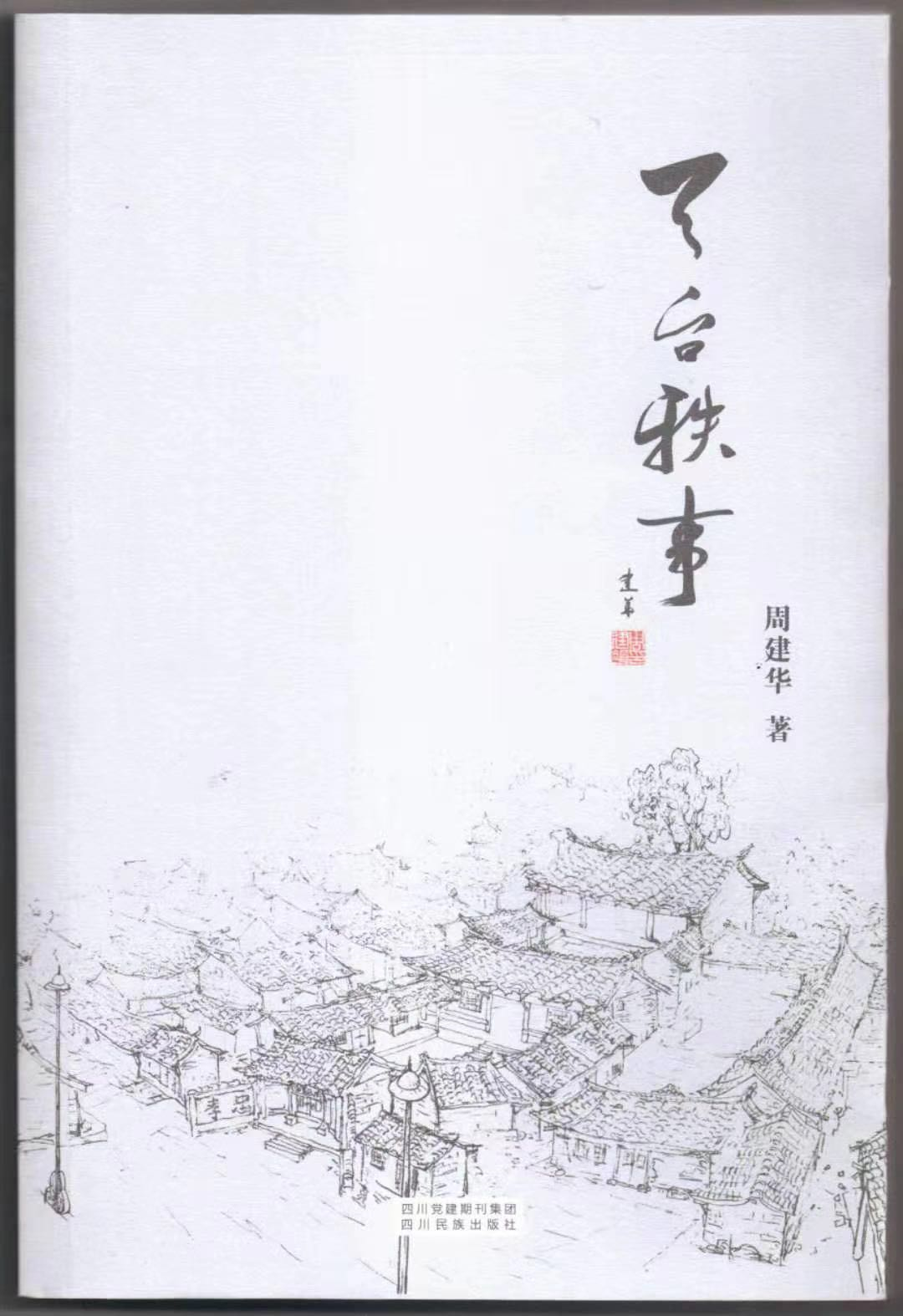
三
有一则广告词(记不清在哪里曾看到的了):人生有时就像一场旅行,我们在乎的不是目的地,而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时的心情。感觉是专为《天台轶事》做注脚。《天台轶事》虽只是作者在对自己一段人生历程的清理,但从中能感觉到周建华在散文创作上的执着与自信,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来看。
第一,于细微内心体验中包容社会、个体、心灵的一切
《天台轶事》收录七十多篇文中,所记之事都是生活中的平常之事、普通之人、常见之景物,都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;通过对其生活中生活事件或某些片段的描述,表达作者的观点、情感。如《突然想养一条狗》《两筐鸡蛋》《向大爷和他的猫》、《三妹和她的餐馆》等,虽不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,但作者对生活的感受是个人化的,情感认知是独特的。
包容心灵、个体、社会乃至宇宙,就是散文的世界。周建华在写作时喜从熟悉的小处着眼,一言一动,一沙一石,及一闪念、一悸动的细微内心体验……进而关照自我,引发读者对个体、社会乃至宇宙的思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第二,文字背后是作者的真性情
《天台轶事》七十多篇散文里,有些是作者直接出场,如《春联轶事》《坐上动车去成都》《生活需要色彩》《青海湖的雨》等;有些则未见作者的身影,如《名字中的五行》《说家谱》《白坟湾的来历》等。无论在与不在,给读者的感受都是作者“无处不在”。
或推心置腹地和读者促膝谈心,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向读者倾吐……感物抒怀也好,触景生情也罢,周建华总是要想办法在字里行间渗入自己的真情。这其实也正是散文书写的独到之处。
第三,回忆性散文的还原书写让文字充满了“现场感”
《天台轶事》中有大量回忆性散文,如《记忆中的
》《桂花酒》《外婆家的杏花树》《月上东山回家记》等。这些从“从记忆中抄出来的”文字, 在内容上糅合了一定的传记成分。过去的时间特别是那些遥远的时间对今天的周建华来说,已成为了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。在这个过去时间的场所中,周建华希望自己能通过回忆,珍视现在的生活……
现在的“我”述说着过去“我”的故事,这其中凝结、蕴含了作者从顽童走向学童、由家乡走向城市、进而外出求学以后的成长体味。读者在品味当时情境中的“我”与事后回忆中“我”之间的情感距离时,有一种亲临其境之感。

四
很显然,《天台轶事》不是周建华的一次精神历险,却是在“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”状态下,对美善、对现实生活丢失已久精神家园的呼唤。作者本人也因此以一个真正意义上作家的圣洁,保持了对文学的虔敬与热爱。
我们也从中欣喜地看到,在这个人人迫于生存压力,局限于眼前狭小的“营营苟苟”、感觉迟钝、总是充满了焦虑的社会里,是文学在引领作家进入到一个更加宽阔的领域,同时也使作家的所思所想成为人们灵魂的安居之所,从而为我们打开一扇意义世界的大门。